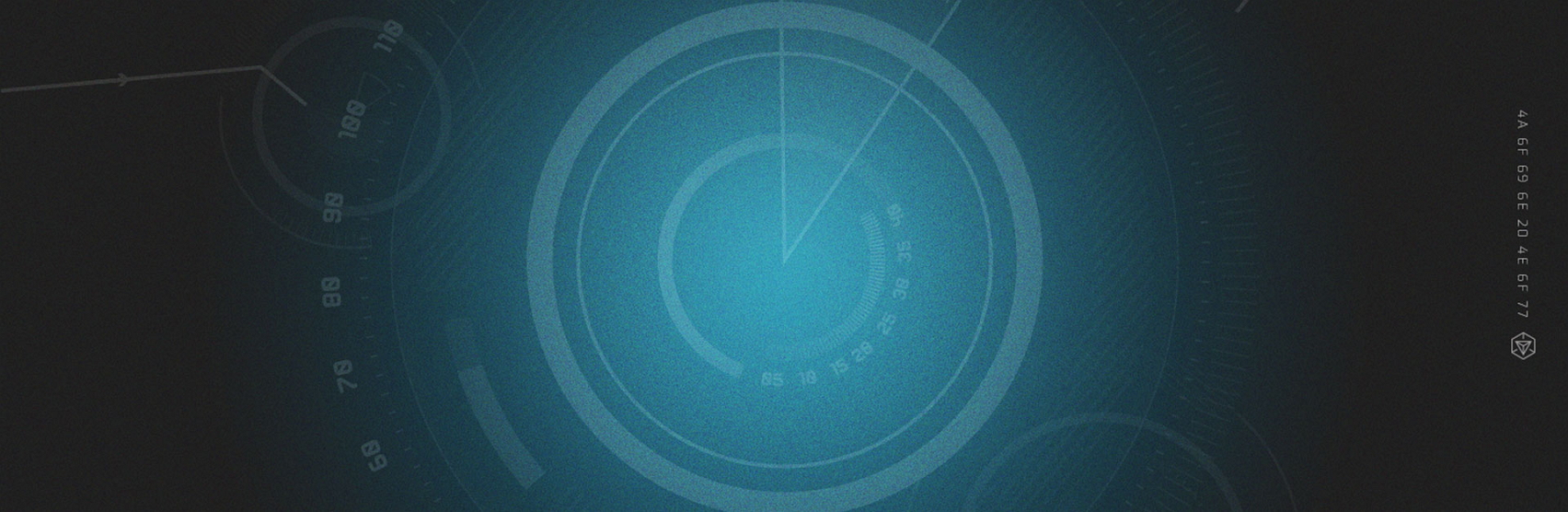点击查看微信稿件原文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 Ingress Beijing
大家好,我是aiqin。或许有些朋友知道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电影,或者愿不愿意看我这又臭又长的转绿自述。
13年入坑,在机缘巧合下被社团学长安利了ingress。在机缘巧合下我选择的是抵抗军,与学长正好是对立。当时学长倒也觉得也挺好,在胶囊没有问世的时候通过疯狂的手速给我把低级脚炸扔了一地。
慢慢的在青岛的唐岛湾畔校园中升级,拿到了founder牌,玩家也越来越多。校园内的情况跟整个青岛的情况差不多。绿军稳稳的压过蓝军一头,本来我是很懒的,就只在学校里上下课的路上刷一刷。校内玩家来来去去,稳定下来的也差不多是我一个抵抗对上四五个启蒙罢了,在学校内多次出现过我单人刷po被一群人“逮捕”的情况,然后一块到北门小店简单吃一顿。在没有ap通胀的年代,学校里一些绿朋友想升升级,只能靠我出来清一下场,连完,他们再继续连。物资当然也会不够,只能请求绿军们投喂。在如此强度下,我倒也成为青岛第一个16的玩家了。
在这期间,岛蓝,一小支抵抗队伍出现,李奶奶,阿白,陈霸王,小彩虹,猫薄荷陆陆续续出现并活跃了起来,我也因为喜欢水群,被邓大取了个小爱爱的外号,还好后来只截取了小爱,也没人深究来源。玩家数量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当时北蓝公众号一条稿子下面数十条评论,有时候甚至评论放不下。各种事件层出不穷。有人会入戏过深,非要争个你死我活。当时我想表达的只是:游戏只是游戏,如果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请停止游戏,回归生活。在大猫出了令人悲痛意外之后,我便再加了一条:过马路不要玩手机。也算是缅怀大猫,和警醒自己,不要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
在15年底的回答中我就这么说了,到现在也一直没有忘记。
回归正题,转绿,对。我为什么要转绿。起因也算是石头。
是啊,游戏都快关服了,能让玩的,也可以去玩玩看看。18年刚出转生功能的时候,我毫不犹豫转生选蓝,基本也没再怎么玩。有些玩家,例如猫薄荷,试探的转到了启蒙阵营。退了所有的群,像一个幽灵在外面飘。23年回到青岛,活跃的玩家也已经不多了,岛蓝社群还一直在,在被石头卷起来刷ap后,缺少对立阵营的游戏也比较难刷了,转生的人越来越多,只是恰好,距离我上次转生也太久了,不如转绿试试。恰好,就加入了转启蒙大军的一员。
为什么选这部电影做标题,绿皮书,讲的是个反歧视的故事。海报又正好,绿皮书,却是个蓝海报。展现包容、和解。感兴趣可以看一看,十分推荐。最近青岛蓝转绿的人数有点多,飞云想加个绿军的招待群,引发了绿军TONOKO大佬的评论:原来是伪军。然后飞出了tg群。
飞师傅没办法,就自己建一个群,插旗包容性更强的启蒙群组。引发了另一位我不知道id的大佬鄙夷,大致意思:我是绿军不是绿皮,才不跟你们玩。然后该玩家在tg 山东抵抗军群组 疯狂输出(用不习惯tg,各种引用与Sticker太眼花缭乱)据我理解,该玩家成为众矢之的有以下几个原因。①大意就是该玩家先前在北绿公众号上发了一篇稿子说WG52O大佬被封了,实际上只是自己打错了ID,把O当做0去跟别人聊天。引发吐槽。有人提出道歉也拒不认错?②指责某些蓝军玩家作弊,并拿不出像出了多号log,只拍到一个人,多方面论证类似证据?③指责蓝军有科技拦截他撤回的言论(实际上tg群组管理员就能看到),莫名其妙抓个人出来对线等奇怪逻辑。
也不会看当前的事实,给出了登录信息,截图背景不一样等自证。也是只管扣帽子。通过拼错id事件,倒也没人会相信道歉一说吧。
在疯狂对线期间,恰好一个回归蓝军nekoKN到青岛一个绿顶点po,碰巧进去并打掉了。该玩家也讽刺蓝军是飞机。绿军大佬Vikingorz也在公屏说是飞机。
nekoKN放出现场图后,tg群林雨便不再说话,也不知道为什么。留下一地鸡毛。
在山东抵抗军频道发现了这么一些说法,作为绿皮也想一块拿出来几句。
连在一起说,在报警事件出来之前,应该也没有想办ifs的想法吧。早在2016年青岛第一次办ifs的时候也是经历了不少困难,不知道当时绿军参加了多少,印象中当时问了一些绿军dalao,态度是拒绝约饭,也拒绝合影。后续我便不知道了。
报警事件发生前,来参加的所有人我都很欢迎,有新人也开心认真的在带。之后的事情我也写过稿子从我的视角看待整件事。(《青岛冲突-混沌约饭群众视角》)所谓的绿军新人恶心退坑,是把那两个新人做的恶心事只字不提啊。还是受到了什么仇恨言论才做出那样的事?报警事件的结果是什么,在花生避免线下接触的情况下,被那两个新人报警污蔑跟踪,在警察未到场之前掏手机录视频还怼到花生脸上。这是被跟踪者应该做的吗?在游戏里先欺凌别人,在自己游戏被欺凌的时候就撒泼打滚报警?最后警察定性是什么,游戏里的事情游戏解决,也并不存在任何跟踪情况。这件事一是有警察定性,二是花生也一直避免线下接触,再是花生不参加线下活动基本不报名ifs。山东蓝军被Vikingorz扣的一手好屎盆子。我在任何稿子,针对玩家也都是个人,不会针对阵营发表言论。颠倒是非,散布仇恨,恶意猜忌,也是我上面提到的一些玩家的所作所为了。如果有玩家受到跟踪和骚扰的可能,我的建议跟警察一样,立马离开游戏,而不会说出被恶心退坑这种话。是人身安全重要还是游戏重要?还是少了可以使唤的小弟表达惋惜?
第二张图,说被盖了石头就会发癫,宣传拉黑。好像还有看到言论说石头被盖了然后买凶花生为打手四处出击。也是挺有意思,在交流无果后石头自己驱车一个多小时到海阳打掉了盖子顶点po,便愉快回家了。管这叫发癫,是指没有让打手花生出动自己去打顶点吗?给新人平等的灌输仇恨,说岛蓝社群约饭聚会水群,吸纳了一些绿军一块进来交流。就影响了绿军社群发展。满是仇恨之地,怎么发展社群。如果想发展的话,也祝愿能发展一个良好的社群吧。
还是那句话,我不善言辞,但偶尔喜欢发表点意见。也希望所有玩家在游戏里可以得到乐趣。如果游戏严重影响到生活,离开游戏是最优的选择。引用石头的一句话,大意是:我想到这个游戏是约饭,聚会。而那些人只会想起骂人、发癫。
哦,这是一篇转绿稿,我为什么转绿。因为我想在游戏里得到一些没得到过的乐趣。希望能继续跟可以一起玩的社群愉快的玩耍。并且平等地歧视双标,恶意扣帽子玩家。-aiqin
Telegram – https://t.me/IngressBeijing
网站 – https://bjres.net(可进行历史文章搜索)
玩家助手 – https://t.me/IngressBeijingGPTbot
投稿后请及时联系我们,联系方式:
Telegram – @alexrowe
QQ – 350259971
Niantic Chat Group – YxR8TEU4
点击查看微信稿件原文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 Ingress Beijing
在炎炎夏日参加了入坑ingress以来的第一次ifs。
今天上海的云很给力,气温(至少是徐家汇公园的)从下午1点开始就逐渐下跌到35度以下,勉强到了能活人的水平()
因为第一次参加所以开始前20分钟到目的地后就开始因为社恐而绕着场地作圆周运动,并与还未谋面的绿军们诚信互刷(x
4点鼓起勇气在公园的北广场签到以后被enl@yumimao塞了个自己家猫咪的无料小卡片。
等到大约4点30因为折返回家拿旗子而迟到的enl@CuteAnemone来了以后,问路人其实是一位agent的小孩拍了张只有enl旗子的合照因为res@Tarcadia也没带))因为有些privacy concern这里就不放出来了qaq))
活动主要是环湖的passcode解密
大家动作都很快而且res@wych42直接私聊给我发passcode了所以很早就领到物资了。有个玩家(enl@JackWorks)当场转生导致自己fevgames上显示升了-12级www。因为到6点物资po才开所以乘着1个小时的间隙去吃了顿12块的晚饭因为社恐怕市区贵而且没太搞清楚情况所以就没和大部队一起约饭,在徐家汇边上用骑行包月卡爽骑(迎面的风挺凉爽的),中途差点没抵挡住诱惑跑去ttw打乌蒙大象(逃)。
在补到358个8炸和54个8糖以后因为手机没电了匆忙离开了现场——坐11号线回家上高架段的时候正好是晚霞最漂亮的时候。
奔忙了一个下午的疲惫也被晚风悄悄吹进了无边的夜色中。
Telegram – https://t.me/IngressBeijing
网站 – https://bjres.net(可进行历史文章搜索)
玩家助手 – https://t.me/IngressBeijingGPTbot
投稿后请及时联系我们,联系方式:
Telegram – @alexrowe
QQ – 350259971
Niantic Chat Group – YxR8TEU4
点击查看微信稿件原文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 Ingress Beijing
苏州ifs好耶~
悔死我了,错过了高个优雅还能带我进苏大的车厘子,望苏大红po场兴叹qwq 只有路上大佬拽的一条条蓝古筝~
但是重点是!车厘子推荐我萌去恰双塔的羊肉,东云龙老师光速攒局,恰到了羊肉和羊羔。笑死我了,约完才发现是在沪蓝群约的,没发现苏州ifs有群我真的笑死。和回坑老玩家萌一起嘎嘎炫噻,不过苏州恰的也好清淡喔,狠狠放生抽、醋和剁椒~
恰完慢悠悠地晚到45分钟,刚好赶上14:15的KFC合照嘿嘿嘿。发完大家的卡,狠狠地介绍了蓬松的“啊哦”耗子哈哈哈哈哈哈哈嘎。
美好的时光就在可爱绿莓不断叫嚣的“蓝军呢?怎么还不炸!”和“不够水润的苏北男人”等金句频发中飞速度过。我光速“来了来了”,甚至要了绿莓姐姐3桶炸,她真好我哭死。猩猩家的游戏嘛:我看着全是脚的时候炸不出东西,我看着一无所有的时候甩炸疯狂爆AP。听起来有点离谱,但如果是猩猩也可以理解。西川学长和小姐姐的CP也太可爱了叭,听他俩聊天就像在讲段子www
好家伙的,16级进度条一下午完成1/6,我都不敢想,这怕不是上半年再参加几个ifs就能升16了。
半场突然看到拉图的脚,火速把拉图拉到楼上KFC叭。
一身军大衣的拉图:你们嘤国留子不是最喜欢这款了吗?
我:你确定不是俄国留子?
旁边的小哥:嚯,你这德式大衣真不错!
拉图:她说这是毛子的(撇嘴)
哈哈哈哈哈哈哈对不起,但是军绿色不看里面红底子嘛哈哈哈哈哈哈哈。
面到了昨天下班就在1公里内活动的小哥!居然有人收集bc要签名耶,“这样就是独特的啦”,真好啊,让咱体会了一把签名的快感。不过没有hack到乌拉飞和0x3等一些路上看到的脚,有点遗憾耶。
印度餐厅晚餐嘿嘿嘿。
拉图:这边都是蓝军,那边除了你都是绿军
我:我是叛徒www
看到各地ifs吃的都好舒服啊,小罗手拿椰树椰汁、蜀蓝拿着公告牌背面真的都好搞笑啊哈哈哈哈哈哈哈!想面大家www
和东云龙老师他们去了诚品书店,社会学板块和旅行板块可爱。后天再来逛逛www
熟悉的平江路和漆黑的小巷子。还是来了这种没个灯也就一米宽的巷子,想不到自己半年前立的flag马上就倒了,还是为了牌子来了。四处转着就又到之前转的好多院子啦~
明天就干掉最后1000分!
谢谢大家创造这么美丽好恰的ifs!
Telegram – https://t.me/IngressBeijing
Twitter – @ingressbeijing
网站 – https://bjres.net(可进行历史文章搜索)
投稿后请及时联系我们,联系方式:
Telegram – @alexrowe
QQ – 350259971
Niantic Chat Group – YxR8TEU4
点击查看微信稿件原文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 Ingress Beijing
这是一个帮助 Leader 快速进行核查确认的小工具。
使用方法
详细使用视频如下:
下载地址:https://testflight.apple.com/join/p130rpK9
(只支持苹果、需要 Testflight)
Bot 账号:sheet-bot@ifstool.iam.gserviceaccount.com
Telegram – https://t.me/IngressBeijing
网站 – https://bjres.net(可进行历史文章搜索)
玩家助手 – https://t.me/IngressBeijingGPTbot
投稿后请及时联系我们,联系方式:
Telegram – @alexrowe
QQ – 350259971
Niantic Chat Group – YxR8TEU4
点击查看微信稿件原文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 Ingress Beijing
多次转生有什么好处么?过去是完全没有的,现在有了那么一点了……
有闲的没事就转生的大佬发现,猩猩的商店里面,除了阳光普照的普通 Cube 之外,还有一个红糖,而这个红糖上面还有一个特殊标志。
我们放大这行小字(确实有点太小了)
可以看到,这个免费红糖的获取要求是:转生超过 5 次。
根据情报,转生 5 次以上的大佬每周都可以从商店里面薅一个红糖出来。
看起来猩猩终于开始尝试给这些肝帝们一些福利,来鼓励更多玩家加入到转生里面而不是到了 16 就躺平看天了。
当然……东西少了点,不过总是个开始了。
Telegram – https://t.me/IngressBeijing
网站 – https://bjres.net(可进行历史文章搜索)
玩家助手 – https://t.me/IngressBeijingGPTbot
投稿后请及时联系我们,联系方式:
Telegram – @alexrowe
QQ – 350259971
Niantic Chat Group – YxR8TEU4
点击查看微信稿件原文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 Ingress Beijing
马上毕业了不在天津了,想着随便整点什么,于是就做了个竹笋。
多年以来,由于portal向外link的总数被限制在40根,在不考虑重叠po的情况下,竹笋最多可以做到六重或伪七重。由于《猩猩宣布准许在Field 内建立2km 内的Link》,通过从field内部向外射出link,现在可以做出真正的七重竹笋。同样由于这一改动,竹笋的link顺序变得更加灵活,做出相同规模竹笋的难度较以往降低了不少。另外,由于《BuriedMemories 全球活动加成已经生效》,hack会获得1.331倍道具,因此画三图全对可以稳定获得2把key,薅key的效率大大提升。
行动区域选在了po密度较高,并且地形相对熟悉的天南大老校区附近,但使用@Nanoape的规划工具求解之后,发现仅凭天南大区域的po不足以支撑七重竹笋,于是把南边的水上公园也考虑进来。天南大以及水上公园都是随意进出的区域,其他po零散的分布在各个小区中以及马路边,仅有水上公园旁边的周邓纪念馆需要提前几天预约才能进入。
该竹笋三底边长度分别为3.35km,2.80km,2.53km
由于po密度较大,整片行动区域相对较小,仅有11根link达到1.95km以上的限制,并且都与最外层的三个一类点相连。因此,这些超长link将从这三个顶点直接射出。其余较短的link全部按照由内向外的顺序连接,所以key的需求量从高级顶点到低级顶点逐级下降。对于二类点“西南联大纪念碑”需要准备93把key,外围的一类点“石狮石鼓”,“母子侧颜”,“六里台桥路灯”需要65把key,而最底层的七类点不需要准备key。在实际薅key过程中,均准备了少量备用key。
6月30日10:00,从天津大学薅完所有需要的key出来,在“六里台桥路灯”准备开连。其实连link的过程很无聊,再加上我没有对路线作提前规划,所以只是一整天在大太阳下面跑来跑去,没什么意思,给大家看看我中午吃的麦门吧。
6月30日25:12,仍然有少量link没连完,干不动了,下班睡觉。
7月1日8:30,继续忙活。
7月1日12:45,正式完工,坐下来喝一杯冰摇红梅黑加仑,好喝,爱喝,多喝。
整个行动过程的gif如下,可惜的是开头因为奇奇怪怪的原因没有录上。
行动总共涉及367个po,准备了1200把key(含备用),行动过程耗时20个小时。即使在link规则相对宽松的当下,七重竹笋仍然要求较高的portal密度。对于单人八重竹笋,由于存在更多超过2km的link,对连线顺序的要求更高,并且所需key的总数超出了一名特工的仓位上限。期待未来其他特工通过现场摸key现场连线等手段,合理管理仓位,做出单人八重竹笋。
一颗立体竹笋,遥远的生殖崇拜,爱来自牛萌萌
感谢规划组@hezc1928,薅key组@hezc1928,行动组@hezc1928,intel组@hezc1928,战报组@hezc1928,没有你们的努力就没有这颗竹笋与这篇战报。
在@Xyinkl的威胁下,感谢该特工友情提供400八炸用于前期清理红po。红po是好文明,清理红po拿到的ap比做竹笋本身还要多,而且还会掉key,减轻薅key压力。
然后这人就在外面xjbl了一坨尾巴,见gif图右上角
插播广告:这么大的竹笋真的不想来看看吗!7月6日天津ifs欢迎您!报名链接:https://fevgames.net/ifs/event/?e=27162
天津ifs宣传海报
发稿日应该就是我的生日了,就把这颗七重竹笋作为我的生日礼物吧。
Telegram – https://t.me/IngressBeijing
网站 – https://bjres.net(可进行历史文章搜索)
玩家助手 – https://t.me/IngressBeijingGPTbot
投稿后请及时联系我们,联系方式:
Telegram – @alexrowe
QQ – 350259971
Niantic Chat Group – YxR8TEU4
点击查看微信稿件原文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 Ingress Beijing
@IFS-CN-Bot 是用于在Telegram群组内显示IFS活动信息的bot
在TG群组内输入 @IFS_CN_bot 等待bot响应
选择想要查看的IFS场次即可
如果你希望生成RSVP按钮 使用
@IFS_CN_bot RSVP
这样生成的响应会附带RSVP按钮 如果在群组内置顶这条消息就可以看到置顶RSVP按钮。
如果你是IFS活动的Leader希望替换默认的预览头图可以前往
https://github.com/ChestnutLUO/ifs-img
仓库提交PR
Telegram – https://t.me/IngressBeijing
网站 – https://bjres.net(可进行历史文章搜索)
玩家助手 – https://t.me/IngressBeijingGPTbot
投稿后请及时联系我们,联系方式:
Telegram – @alexrowe
QQ – 350259971
Niantic Chat Group – YxR8TEU4
点击查看微信稿件原文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 Ingress Beijing
事情要从5月19日说起,@whitevivid端掉了绿军@BH4UMN和@BI4UMC在精益广场维持的绿block。@CI2VO5IXZ7同步从泰州link丹阳活动广场,然后奔袭盱眙服务区,完成了多年的夙愿,从盱眙服务区做控场,达成了盖扬州的目标。这个控场留给了南蓝一个很好的底边,一个很好的盖南京的底边。
@whitevivid作为一个日常关注intel地图的玩家,发现只需要等待友军的众多link烂掉(果然最大的block就是友军的link),就可以实现在板桥盖南京的计划,顺便给@knowgg和回坑萌新@Brightmooner送上一枚控场黑牌。
由于蓝block太多,遂请求@cissyan,@hacierpak,@xiyouyuedui,@Brightmooner,@knwogg停止充电,逐步掉电断link(埋下伏笔)。夜长梦多,在局势逐渐明朗的intel地图上,绿军@DH99,也嗅到一丝可行的气息,实行着他的计划。
时间跳转到5月30日行动当天,@knwogg载@Brightmooner到板桥就位,@whitevivid到翠屏山清障。就在清障结束的15min前,意外情况发生了,盱眙服务区的顶点po没了,原来是@DH99从仙林奔袭盱眙服务区,执行他的计划了(后话)。intel组@xiyouyuedui开始分析局势,推断@DH99也要从某个地盖南京。既然计划的顶点已经没了,@xiyouyuedui迅速在工大XJBL,拉起了众多条防御link。期间@DH99又出现了在洪泽湖旁的盱眙县占了po,link了南京汤山,“吃上了盱眙龙虾”。
就在大家以为行动暂告段落,@DH99又出现在星火路药谷清障(工大XJBL),然后又一路向南,@DH99以15min快速通过长江的速度,单枪匹马地在长江南岸北岸清障,但是清障的速度仍然赶不上分散在4地Agent XJBL的速度,最终停步于@majorgoh楼下。
蓝绿极限拉扯,互相成就,都没拿到控场黑牌。
Telegram – https://t.me/IngressBeijing
网站 – https://bjres.net(可进行历史文章搜索)
玩家助手 – https://t.me/IngressBeijingGPTbot
投稿后请及时联系我们,联系方式:
Telegram – @alexrowe
QQ – 350259971
Niantic Chat Group – YxR8TEU4